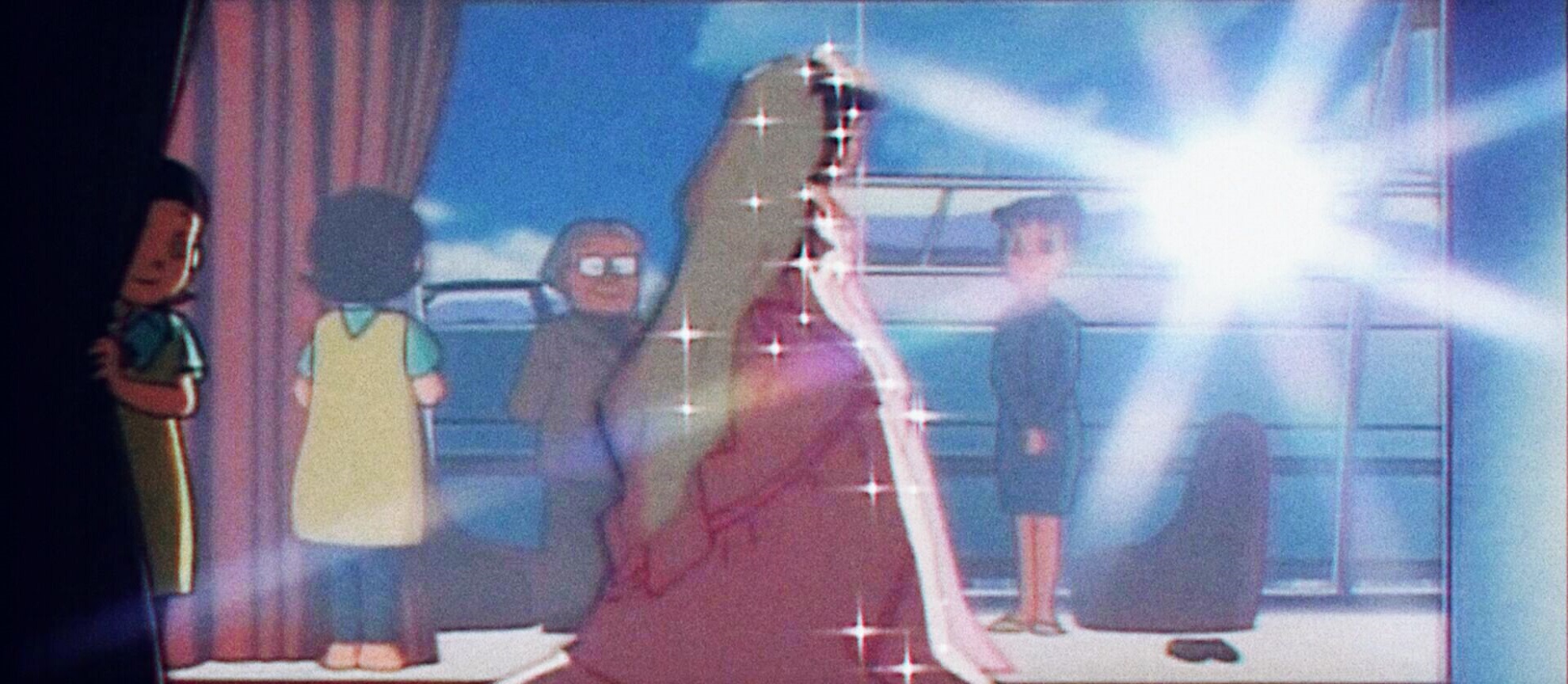兩年前,我對大家說:「我有一段清淡如茶的故事,你願意聽嗎?」 兩年後,這段故事終於講完了。 那個時候的各位,還有誰在嗎?
序
清晨、上午、正晌、下午、黃昏、夜晚。
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壯年、老年······
墨空微明
「大家……大家都在哪兒啊!」動物園裏,一名男童和同學走散了,只得四處亂跑,試着找到隊伍。跑着,跑着,跑得氣喘吁吁。他還沒有找到同伴,卻撞上了一頭猛獸。籠子裏的雄獅沖他咆哮,好像要將他撕碎一樣。
他的膽子很小。粗魯的同學、狂吠的野狗、甚至可以輕輕碾死的蟲子,都是他所畏懼的對象。更不用說壯年雄獅——即使是被關在籠子裏的雄獅。
被嚇出的一股眼淚開始在眼眶裏打轉。
他像逃命一樣,緊閉着眼睛跑開,誤打誤撞地衝到了小樹林裏。
男孩撞到了一顆掛滿了蟲子的樹。樹晃了晃。蟄伏在枝葉上的蟲子如雨而落。
「蟲···蟲子!」他被嚇得沒法繼續站穩,搖搖晃晃,最後一屁股跌倒在地上。
男童再也忍不住心裏的驚悚。
「嗚哇——!」
他死死地閉着眼睛,淚水嘩嘩落下。
恐懼飛快地擴散着,很快覆蓋了整個心底。
他看到的天空被潑上了一層濃重的黑墨;他看到的世界陷入了完全的混沌與黑暗。
聽着聲音,她小心地尋了過來。
女孩子和蟲類,好像從來就沒有交好過。顯然,她也很害怕那散落一地的、在地上扭曲着蠕動的大蟲。她顫顫巍巍地看着地面上那群長滿觸角的蟲子,仿佛一座隨時會崩塌的雕像。
不知道是因為他是朋友,還是因為他是弱者。一股力量湧現在女孩的心頭,驅使她動了起來。
她用力地擠了擠眼,試圖將眼睛旁的淚水和恐懼一併擦乾。她伸手撿起地上的樹枝,竭盡全力地、一把把掃飛了地上的大蟲。
「看,不怕不怕。」
她伸出手,他搭上。荏弱的男童跟着掌心中的溫度,快步跑出了樹林。
當他再次睜開眼睛時,那些眼淚已經乾涸了。天空上的黑墨已經和膽怯一起被沖干,雲彩像被洗滌過一般清淨。
如沐晨風
「唔···這是···」她用手指輕輕地點了點浴缸的水面,隨後懷着好奇探了進去。
「水面」的另外一邊,就是另外一個世界了。有趣的是,在這個世界,僅有的人類倒沒有什麼攻擊性,而一向按照邏輯做事的機械卻狂暴得異常。
好奇心讓她踱步走出浴室。她的前腳剛踏出去,屋子裏便倏地衝出一架面露猙獰的鐵架,以一種非常詭異的方式運動着。她被嚇得慌忙用手捂住了口,免得自己發出崩潰的尖叫。
她一步步後退,鐵架卻猛地殺了過來。
「啊——!」她蜷縮在牆角,尖叫起來。
「轟!」
一股極強的氣流從女孩的臉旁划過,以不可抵擋之勢轟飛了那副猙獰的機械。
帶着手炮的男孩男孩背對陽光,屹立在門前。
女孩掛着恐懼的淚沖了過去,緊緊地抱住了他。
「沒事,我在的。」
他伸出手,她搭上。
她跟着心底的安全感,跑向了陽光照耀着的屋外。
驕陽似火
「······」中午,一名本來應該在榻榻米上酣睡的男生此時卻坐在窗邊,心事重重。
明天就是暑假的最後一天了。
他寫完了暑假作業。所有人都不能不認定這是一個奇蹟。
「我回來了。」一名藍色的機械人走了過來。
「嗯···」男生抬起頭看了一眼,悲傷讓他的睫毛遮住了眼眸,「和小咪···已經說了再見了吧···」
「嗯···」它說,「別太傷心了···這一天遲早都會來的。」它撐着笑容說。
「對了」,它突然想起了什麼,說,「明天就開學了,你的暑假作業···」
「一個月以前就寫完了···我想一個人靜一靜···」
「好吧···」說罷,它便垂着頭走出了屋子,他繼續把頭埋在懷裏。
傍晚 廚房
「明天就要走了嗎?」雖然已經確定了這個消息,少年的媽媽還是抱着一點僥倖地問到。
「是啊···雖然我也不想的,不過他已經長大了,已經能自己寫完作業了呢。」它安靜地笑着回應道。
「這麼多年來,承蒙你的照顧了。」飯桌前,沒有拿着報紙的爸爸開口說。
「哪裏···我才要抱歉,這些年來給你們添了這麼多麻煩。」它撓着頭說。
「······」他什麼都沒有說,只是埋着頭吃飯。
次日 清晨 臥室
「誒···」它從壁櫥里下來,驚異地發現少年已經不見了蹤影。
它心頭湧出一股說不出的酸楚。即使知道他的消失可能只是為了彼此都不要難過,即使知道自己今天一定要走。
晨曦印到榻榻米上。一室暖意。
心海冰涼。
它拿起早已收拾好的行李。媽媽給它準備了滿滿一盒它第一次來到這個房間時所吃的那種年糕。除此之外,朋友們給它送來的一盒手工烤制的曲奇餅、一張某個不出名明星的簽名唱片、和一張伊藤翼的簽名照,也都在其中。
它掛着兩行淚流,最後一次看着這陽光瀰漫的小屋。
大概十分鐘過去,時間把抽屜一點一點地合上。
咔噠一聲。隨後是腳踏在樓梯上的咚咚聲。
「我回來了!」男生飛奔回了家,手裏拿着滿滿一袋銅鑼燒。他等不及脫鞋換襪、等不及打開臥室的門,便沖屋裏高喊:「看!我今天早晨四點起來幫你買的!這是你最喜歡的那一家銅鑼······」
除了家具、陽光和空氣,榻榻米上什麼都沒有。
他剛剛上揚的手臂同他的身軀一起僵直在晨光中。他的臉部肌肉抽搐着,表情在歡悅和哀傷中掙扎了片刻,最終定格在扭曲的悲切里。
男生跪倒在書桌前,哭得清淚成河。
童年所有的夢在一瞬間凝固了起來,被眼淚一滴滴撞碎,順流漂到未知的遠處。
一轉眼,又過去了數年。幼稚和童真已經徹底不再屬於那少年。
東京 上午 晴
男子站在花店前,認真觀察着花瓣前的露珠。女子在店裏閉上眼睛,細細地聞着馥郁花香。
「小姐,您來買花,是為了準備什麼事呢?」二十出頭的店員女孩笑着湊了上來。
「嗯······我只是想看看罷了。這是丁香嗎?」
「嗯,對的。丁香花象徵着光輝呢。」
「那這個呢?」
「這是百合啊。」
「那百合花象徵着什麼呢?」
「百合花有很多種顏色,不同顏色的百合有不同的象徵意義。您現在看的白百合是純潔的象徵。」
「咦,我還沒有見過這麼多種顏色的玫瑰呢。」她又去輕捻起一旁的白玫瑰,呢喃道。
「嗯,現在大家都已經不太執着於紅色了,這幾個月藍色妖姬倒是很受情侶們的歡迎。」
「唉……太妖艷了,女孩子還是樸實一點好。」
「各有所愛嘛。」
「誒,這是什麼花啊?我好像從來都沒見過呢。」
「這個啊,這是鳶尾花。」
「哦~我曾經讀過一首關於鳶尾花的情詩呢。」
「是什麼呢?」一串交流下來,店員非但沒有急躁,反而饒有興趣地和女子攀談了起來。
「會唱歌的鳶尾花。我以前翻譯國外詩歌的時候讀到過,很喜歡。」
「下班以後我一定會去翻翻看的。」
「嗯。」
女子轉身拿起另外一朵淡黃色的花,問:「這花……我似乎在哪裏見過的。」
「這是夾竹桃啦。黃色的夾竹桃象徵着深刻的友情,相似的還有黃色鳶尾花,它的花語是友誼永固。」
女子又盯着鳶尾花看了一陣子,突然從花海里回過神說:「啊…耽誤你這麼久的工作時間真是抱歉。我想預定一束玫瑰花,30朵,顏色淡一些的那幾種配在一起就好。」
「嗯,知道了,什麼時候來取呢?」
「九天後吧。」
「好的。」
十日後 婚禮現場
窗外,兩隻喜鵲在驕陽下相繼劃出兩道優美的曲線。
屋裏,一簇簇紫羅蘭在紅毯旁綻放着它們一生中最美的嬌容。瓦格納婚禮進行曲的旋律飄揚在空中。
「快看!他們來了!」大個子男子指着廳門,用粗獷的聲音喊到。
「誒?」小個子男子和文質彬彬的男子迅速回過了頭。兩人身上都有一種超凡脫俗的氣質,不過一種是市場的給予,一種是知識的沉澱。
姽嫿的新娘被籠罩在如夢一般柔和的婚紗里,挽着愛人的手臂,緩慢而莊重地走向婚禮的舞台。
歡呼聲在廳堂里迴蕩。
婚禮在聲聲高呼中如計劃進行。
······
等到司儀說出一句話的時候,全場霎時安靜下來,所有人都懷着愛和祝福屏息凝神。
「Will you love her, comfort her, honour and protect her,and, forsaking allothers, be faithful to her,so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? 」
「Yes………………」
沒有人聽到了後面的話,因為話音全部被掩埋在祝福的呼聲中。
香檳,戒指,素色玫瑰,都被籠罩在微微發燙的驕陽里。
當呼聲沉下來的時候,新郎新娘相伴着走下了台。
那一刻,
他,迎着花瓣,面若凝脂。
她,浸着祝福,笑靨如花。
午後清茶
男子打了個哈欠,從臥室里懶洋洋地走了出來。
窗外的陽光也懶洋洋地從臥室走出來。
「爸,我中午飯還沒吃呢。現在都十二點了。」在電視前面拿着手柄玩遊戲機的孩子轉過頭來說。
「唔啊——我知道了,這就去。」男子痛快地伸了個懶腰說。
三十分鐘後
男孩「跐溜」一聲吸起碗裏的方便麵,頂着這個年紀不該有的惆悵問父親:「老爸,媽媽下次什麼時候回來啊?」
孩子的母親是一名外交官,常年在外奔波,回家的次數少之又少。這也使得男孩在電視上看到媽媽的頻率比在家裏都多。
「我也不知道啊···」男子滿臉無奈地說,「不過···你媽媽做的是對社會很有意義的大事,我們應該支持她的。」
他的妻子經常在各國間奔走,即使是懷孕也只讓她消停了一年。
「大事···媽媽很厲害嗎?」
「嗯,是啊。」
「比電視上那些拯救世界的大英雄還厲害嗎?」
「嗯···是的,他們對付的是幻想中的外族侵略,***媽的工作是為了讓咱們人自己別內訌。沒有媽媽這樣的人,世界上的人就可能會相互傷害。」男子似乎想起了什麼,半吊子似的拿起手裏的茶,翻了個白眼說,「何況你媽又不是沒救過世界···次數比那些『英雄』也少不到哪去···」
孩子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,追問道:「為什麼人們要自己傷害自己啊?」
「不知道。」男子應付了一聲,想了想還是添了一句家長的標準對白:「你長大了就會明白的。」
半年後 深夜
妻子已經半個月沒有回家了,不過男子並不着急,因為這也已經算是常事了。
四季春的旋律從手機中飄揚出來,吵醒了酣睡着的男子。
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,把那塊快把眼睛亮壞掉的手機屏幕拿到面前。
隨後他便瞪大了眼睛,趕忙接聽。
手機屏幕上寫着:「來電人:妻 上次通話時間:三個月前。」
「餵、喂!」男子貼着手機說:「怎麼了?」
可對面卻傳來了一名中年男人的聲音:「您好,請問您是這位女士的家人嗎?」
「嗯,對,我是他愛人。什麼事?!」男子開始胡思亂想一些不好的事情——車禍、謀殺、突發疾病等等。
「她在我的麵館里喝醉了酒,現在睡着不醒,你快來把她接回去吧。店面在市文物館旁邊,你來了就能看到。」
「好的,我知道了,真是抱歉,給你們添麻煩了。」男子用肩膀和耳朵夾住電話,慌慌張張地開始穿衣服。
「沒事,請您儘快!」
男子頂着霓虹燈的照耀、在空曠的馬路上驅車飛馳。
十二分鐘後,男子把昏睡的妻子扶到車裏。途中,醉酒的女人嗚嗚索索地說着什麼,像是在傾訴,又像是在抽泣。
「我···唔···辭···」
「什麼?」男子被一股刺鼻的酒味熏到了,用手捂住鼻子。
「······」
「唉···」男子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今天晚上發生的事情太反常了。說實話,他從小到大都沒有想過,自己的妻子會半夜醉酒。
男子上一次嘆氣是在昨天,他在翻抽屜的時候碰巧看到了妻子以前翻譯過的詩集,詩集中還夾着一本摘抄本。或許是一時興起,男子拿起筆,在本子上認真抄下這樣一段詩。
是一場風景,一盞燈,
把我們聯繫在一起,
是另一場風景,另一盞燈,
使我們再分東西,
不怕天涯海角,
豈在朝朝夕夕,
你在我的航程上,
我在你的視野里。
次日 清晨
天氣陰沉沉的,男人的妻兒都還在睡着。他覺得很心慌。
男人穿好衣服去廚房。
「咳···兒子!起來吃飯!」
「哦···我這就穿衣服。」
「快點···恩?」
頭髮散亂的妻子依着主臥的房門,看着他。
「那個···嗯···飯做好了···快吃吧。」
女子行屍走肉般走向餐桌,拿起筷子,吃起早飯。
「額···對了···昨天你為什么喝那麼多酒啊···你不是從來都不喝酒的嗎?」
確實,他的妻子很少喝酒,即使在婚禮上也只喝了一點點。
女子沉默着拿起遙控器,把電視打開。
男子看着今日頭條新聞,感覺甚至有些驚悚。
電視屏幕上赫然顯示着——「外交官離職」
「什麼!?你辭職了?」
「不是···我只是···唉···肯定不能待下去了。」
「為什麼?」
「我的理念和上面的想法不一樣了。就這樣了。」
男子驚愕得說不出話來,只得低着頭,讓屋子再次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中。
男子思索了一會兒,問:「那···你以後要做什麼呢?」
「不知道,反正不會再像之前那樣了,到最後都是徒勞。可能,當老師也不錯吧。」女子強顏歡笑着說。
「唔···嗯。」男孩還沒有徹底醒過來,眯着眼睛看向餐桌,然後像通了電的機械人一般,飛也似地撲到母親的懷裏。
女子的笑容自然了不少,她輕撫着孩子的話,他從小到大都沒有想過,自己的妻子會半夜醉酒。
時隔六年,從這一刻開始,這間屋子再一次成了名副其實的「家」。
夜晚,女子拿起久違的摘抄本,笑着抄下了這樣一句話。
我的憂傷因為你的照耀
升起一圈淡淡的光輪。
今天晚上,夫妻倆的幾個朋友快把家裏的電話打爆了,最後男子乾脆把電話線拔掉,直接回了電話。
一番安慰,一聲安好,又是一番安慰······
最後朋友們要請他們出去吃飯。這所飯店着實不一般,無論是不是淡季,飯店都一直是滿客。這不僅要歸功於那位高大朋友的超市和牧場所提供的放心食材、那位學識淵博的朋友超凡的設計所帶來的新意,還有那位矮個子朋友的、龐大的資金支持和信譽保證。
「媽媽,我不想出去,我想讓你給我念書。」
男子很驚訝。以前,這個孩子就算玩遊戲玩到睡着,也不會去把那些故事書翻上哪怕一頁的。
自從母親和孩子四目相對的那一剎那開始,女子就開始後悔,後悔自己為什麼數年來一直忙於奔波。她已經欠下自己的孩子難以償還的愛和陪伴。這些彌足珍貴的事物,是時候還給孩子了。
半夜,男子醉醺醺地打開房門,踉踉蹌蹌地晃到主臥。不過屋子裏面黑漆漆的,沒有人醒着。
他先是下意識地一驚,隨後小心翼翼地推開次臥的門。他的神色安然下來。
迎着微弱的月光,他看到妻子睡着的妻子摟着六歲大的孩子。男孩的面容如浸過蜜漿一樣。即使是在睡夢中,孩子的喜悅也溢出了身體,充斥在房間的空氣里。不得不說,這是自孩子出生以來,他所看到過的最溫暖的瞬間。
男子輕輕地關上門,唯恐發出半點聲響,驚擾到這夢似的圖畫。
回到自己的屋子裏,男子打開桌子抽屜,裏面翻出一張字條。
「爸爸,今天我看到媽媽哭了,很傷心。她不告訴我為什麼。」
男子心裏一涼,隨後嘴角微微上揚。他拿起紙和筆,在抄錄本上輕輕地抄下了這樣一段詩。
我們分擔寒潮、風雷、霹靂;
我們共享霧靄、流嵐、虹霓。
仿佛永遠分離,
卻又終身相依。
他不知道自己是該憂傷還是該快樂
他應該傷感,因為妻子已經不再像她自己所期望的那樣貞高絕俗了。
他也應該快樂,因為妻子真的在逐漸變成孩子的母親——正如她自己所期望的那樣。
她再也不用每天都為了對付那些雲翻雨覆的人而夢斷魂勞。
他再也不用每周都因為擔心妻子的身體而枯腦焦心。
他再也不用每月都因為缺少來自媽媽的關懷而一夕數驚。從今天開始,他成了媽媽的寶物。
隨後男子便自己一個人睡了。他不知道這種蔗漿拌糖般的生活能持續多久,但他相信,自己能為了這個家,撐起一片天——一片描繪着童真與夢想的,洋溢着溫馨和愛意的,無邊無際的蔚藍色的天。
三日後
家裏的電話再一次被打爆,但這些人卻沒有前幾天的朋友那麼友善了。
這些人是來追問離職的事的,關於原因、計劃,甚至出現了「陰謀」這種辭說。
女子決定不予理睬,世界上總有些喜歡對別人加以「揣測」的閒人,她完全沒有必要去滿足這些人病態的心理——反正說實話也不會有多少人信。清者自清。至於閒人們怎麼想,那就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了。
女子想到這些,輕輕地笑了笑,便回房休息了。
一架飛機飛過太平洋。
當東京仍繁星璀璨時,夏威夷艷陽高升。
一家人起來看日出。微涼的晨風拂過發梢的間隙,略暖的第一縷陽光,斗膽射入人間,海面磷光如蟻。
手機很不識趣地打破了寂靜之音。
男子拿起手機一看,是一條來自國內的短訊。
「知道你們在夏威夷,好好玩,回來之後儘快到我這兒來一趟,有一部紀錄片需要你們參與。」
雖然是匿名消息,但刻意加上的位置信息已經將發信人的名字暴露得明明白白。
位置:英才實驗樓。
一個月後,一部紀錄片轟動了整個亞洲。
庸人安靜了下來。
一對夫妻飛過時間海。
日薄西山
「唔···」老人揉了揉眼睛,看着尚未被刷亮的天空,他不是很利索地穿好了衣服。因為剛剛過了穀雨,天氣已經非常暖和了,老人只穿上了相對較輕薄的衣服,就去洗漱了。
老人熱了熱昨晚燉好的鱧魚湯,用顫抖的手拿着勺子,把它一勺一勺地盛到了飯桶里。
幾滴湯灑到了灶台上。
老人的腿腳並不是很靈便,但總的來說還湊合。他緩緩地下了樓,走向醫院的時候,街道上的行人寥寥無幾。
醫院裏的一切好像都是白的。
一位老婦人在病床上安詳地躺着,仿佛她從未被疾病折磨,而只是在享受閒適的生活一樣。
「孩子,你先回去吧,我來看着你媽。好好休息休息,明天還要上班呢,啊。」
「知道了,爸。」
男人的壓力看着並不比病人小,他的眼眶泛黑,皮膚的凹陷圍起來的地方佈滿血絲。
老人的孫子正處青春期。叛逆和張揚是這個年齡段的標籤。孫子和一名女同學談戀愛。家長反對。他一怒之下便拎着行李箱離開了家。
想起這些事,老人哀嘆了一口氣。
窗外,旭日東升。
初夏的晨光和溫柔毫不相干。太陽頹唐地緩緩升起,卻將病房門邊黃白相間的花束照耀得生機勃勃,好像它們還在泥土裏成長着似的。
老人顫顫巍巍地打理好了一切。
「老頭子……」
「嗯?怎麼了?」
「帶我出去看看吧。」
老人用手抵住了胸口,沉默一會兒後,張口輕聲說:「可是你的病…」老人哽咽了一陣,「還是…」
老婦祥和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;」唉,我都知道,都知道……我就想啊,走之前,能再看看咱們,住了一輩子的鎮子,就行了。」
又是一陣沉默。病房比墓園還安靜。
「好。」
然後,四周只剩下心跳和呼吸的聲音。
「老頭子,這個地方……」輪椅上的老人頓了頓,「以前是空地吧?」
「對,咱倆結婚以前,這兒就已經被改成公園了。」
空地改成公園的時候擴大了地方。可現在,偌大的公園裏,只有幾個孩子在一起玩。剩下的,都是些腿腳不很靈便的老人。
輪椅上的老婆婆聽到了很模糊的聲音。可能人老了以後,腦子都會不中用吧。
「看!這是我表哥新做的遙控車,它身上的每個零件都是法國產的。」
「給我玩玩!」
「好啊。」
「我也要我也要!」
「不!你不行。遙控車會被你弄壞的!」
「誒,怎麼這樣?」
「你們別這樣。」
「嗚嗚……」
「別傷心了,到我家一起去做曲奇餅吧。」
「真的嗎?」
「嗯!要去嗎?」
「嗯嗯!」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「啊啊啊,別這樣胡亂操作啊!會弄壞的!」
「囉嗦!」
Bang!
「啊!我的遙控車!」
「這麼多廢話!你是不是忘了,你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,我的東西還是我的東西!」
灼眼的陽光讓人看不清街景。朦朧中的這座公園,好像還是那片空地。公園裏蹣跚的老人們,好像那些年,那些追逐打鬧的少年。
寧夏
不久以後,老婦去世了。
聽到消息的老人安靜地走到病房門口,泣不成聲。
老人自己也記不清,為了竭力向別人宣告自己受到的委屈,自己一生中嚎啕大哭過多少回。但他很清楚,只有四次,悲傷淹沒了聲音,其中三次分別給了三位婦人的葬禮。
遵從逝者的遺願,有關葬禮的一切從簡。醫院後花園一處不起眼的地方多了幾株丁香。那一天,他們的孫子仍然沒有回來。
又一年過去。
當年那名氣勢洶洶的孩子王,現在已經老得不成樣子,連拳頭也揮不起來了。以前那位對科學抱有無限嚮往的少年,現在很少去拿筆了。而那個能說會道的公子哥,現在常常一個人坐在陽台上曬太陽,一坐就是一下午。
不知是不是巧合,幾乎在一年後的同一天,老人安詳地離開了。他在房間裏對着夕陽小憩了一會兒,然後再也沒有醒過來。
整理遺物時,兒子在枕頭下發現了一封信。是老人的筆記,但卻意外的工整。
兒子:
你媽走後,孩子回來過一趟。他哭得很厲害,沒有你想的那麼無情。女孩兒我也見過了,她是能為了別人的悲傷而悲傷的女孩兒。他認錯了。出走並不是為了氣你,只是自己太倔了。孩子要是再回來,千萬別罵他們了。
爸爸一輩子過的都不富裕,也沒太多東西能留給你。信封里有些錢,如果野比家有後人錯買了一隻機器貓回來,那就用這筆錢付賬吧。
有些人,無論多麼艷麗,也只是生命中轉瞬即逝的煙火。
有些人,無論多麼平凡,也會是記憶里的一段感動。
而僅有一個人,能成為這段句子裏永恆的賓語。
I will love her, comfort her, honor and protect her, and, forsakingall others, be faithful to her so long as we both shall live.
結束語
一開始寫這篇文章,是在差不多兩年前的這個時候。
那個時候,貼吧里出現了海量的文章。看上去幾乎所有人都要寫超長篇。但是,在這個地方,長篇不僅寫得很混亂,而且幾乎沒有人把自己寫的開頭完結過。哪怕是最後強制以短篇的字數終結。
其實我也沒有讀過多少文學書籍。當時的我,只是想試着寫點自己喜歡的文字出來。可惜後來因為現實生活的忙碌和網絡上一些煩心的事情,文章也一直被耽擱了。
兩年過去,可以說物是人非了。
帖子都在,可惜不管幼稚還是成熟、情商高還是低,那些發帖的樓主們都已經不見了。我也是一樣。
兩年了,雖然結局寫得還是非常倉促,但這樣應該也可以了。
最後那段話其實是兩年前就已經想好的。期間想過很多不錯的結尾,但很可惜,我也記不起來了。
算是給現在的貼吧貢獻一些內容,也算是給自己一個交代了。